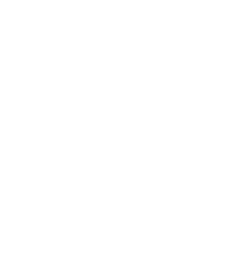菜中“草莽”,我说的是雪里蕻。
称雪里蕻为草莽,没有贬低的意思。我反而觉得,“草莽”二字就是为它量身定做一般恰当——植株密生,叶片宽大,价钱还低。再一次佩服汉语的博大精深,因为有关草莽的字面含义,雪里蕻就占了一半。
前阵子疫情吃紧,好些人忙着囤菜,菜市场上连白菜、萝卜也成了抢手货。然而,市场拐角的地上,码放着几捆雪里蕻,碧绿碧绿,望上去醒目、舒适。一个老婆婆停下脚步,头发花白的她先压低身子,再用指甲掐掐,里外翻几下,然后才开始搞价:“别八毛了,六毛。你看看,满大街除了我,谁还买这种菜呀?就这,回家孩子们又要嚷我呢。”的确,在我看来,除了腌咸菜,雪里蕻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吃法。“不中,上午还卖一块呢,这可是好菜呀。”老爷子摇头,却又舍不得放走这笔买卖。当老婆婆佝偻着背影抱着一蓬碧绿,缓缓朝巷子深处走去时,老爷子仍然在嘟囔:“唉,明年说啥都不种了,还不够力气钱……”是的,无论是三四十年前,或是现在,雪里蕻大约是最不值钱的蔬菜。
这几年,老家的菜地越发少了,更没人舍得用金贵的土地种植雪里蕻,虽然它产量高、易拾掇、不择土性。但我感觉最主要的一点,还是因为它价格轻贱。在我小时候,雪里蕻可是好菜。漫长的冬天,早晚两顿稀饭,我都靠它来唤醒肠胃。有雪里蕻在,藜芥疙瘩咸菜我是看不上的。因为我爸腌的雪里蕻,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绿,好吃还好看。瓷缸里捞出一把切碎,什么调料都不放,就非常下饭。
我特别喜欢咀嚼雪里蕻的根茎,脆,还不失韧劲儿。尤其是雪里蕻的汁液,咸香回甘,自带一股特别的香味。叶片好像扭曲的茶叶,盐渍后非常绵软,入口是另一种感受。夹一撮雪里蕻,放在稠乎乎的玉米糁粥上,嗞溜一口,一个坑。再放,再嗞溜,又是一个坑——有了雪里蕻的加持,无论是粗粝的玉米糁汤,还是塞牙缝的小米粥,都变得容易下咽了。
我爸个子高,身体不好,但做事非常有耐心,比如腌雪里蕻。立冬前后,天气凉了。我爸说,这时候腌菜最好。把雪里蕻从地里收割回来,一棵棵摘去黄叶,拍打去泥土,然后让它们骑在绳子上,而不像村里某些人先淘洗再晾晒。我爸说,新鲜的雪里蕻,茎叶容易折断,香气也会跑掉,样子更不好看。挂满雪里蕻的绳子,仿佛一堵悬空而蓬松的绿墙。它在日头下随风摇摆,摆来摆去;不消半天工夫,墙便单薄了些,颜色也变得黯淡。用手一摸,前半晌还支棱棱脆生生的雪里蕻,像是被日头和风抽去了筋骨。
“晾好了吧?”我总是这样心急。我爸却说:“莫急,莫急,心急吃不了好腌菜。”终于,当茎条软成会打弯的面条时,我爸才开始淘洗它们,一棵棵地洗。身形变得细溜的雪里蕻,从清水里捞出来,仿若柔韧的水草,闪着绿油油的光辉。趁着日头还没下山,再一次让它们骑在绳子上控水。
第二天下午,开始腌菜。“腌菜要舍得盐。”我爸说。一大团雪里蕻盘在我爸手里,再没有一点脾气,被按在粗盐堆里用力反复揉搓,直到茎叶像是烫熟一般,我爸才会停手。只有这样,雪里蕻才会入味,才会碧绿。装坛了。洗净控干的瓷坛,终于盼来了生命充盈的一刻。一定要码瓷实,坛子更不能沾生水或者油渍——这是我爸腌菜的又一条成功秘诀。坛子封好,放在阴凉处,我爸才满意地掸掸衣襟,像是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我爸心里,解决好家人一冬一春的吃菜问题,的确是件大事。
说来奇怪,本已失去本色的雪里蕻,经过时间和粗盐的腌渍,重新变成绿色,而且绿得不再张扬,是一种成熟饱满的绿——多像一个性格莽撞的年轻人,经过岁月的磨砺,才渐渐散发出沉稳醇厚的气质。(杨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