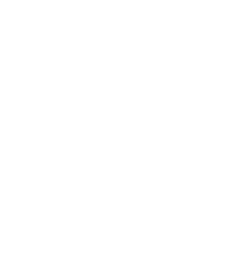哦,伊席次仁啊
□力格登 作品
哈达奇·刚 译
我很羡慕三叔射酒瓶的本领,自己也想试一试。一天,我把好哭、好流鼻涕、嘴馋、脸脏、豁牙子、光腚组成的队伍集合起来,每人带一个空酒瓶来到了野外。说实在的,我多想用三叔的手枪打呵。可挎在三叔屁股上的那支枪,我只能眼看,不敢手碰。现在打瓶子只好用伊席次仁的投石器。我投了几下不行,石头不知哪去了。娃娃军的人挨个儿投,也都没投中。光腚全帕拉更没门,差点碰伤了自己的脑袋。最后,轮到了伊席次仁。
我学着三叔的样子,手指左边第一个酒瓶,喊:“这是敌人。打!”
伊席次仁把投石器摇成圆圈,越摇越快,石头猛然嗖地飞出,只听砰的一声酒瓶成了碎块。
“把敌人挨着个儿消灭。打!”我继续下令。
可这次伊席次仁不投了。
“打!”我又一次下令。
他仍然站着不动,嘟嘟哝哝地说:“多可惜的酒瓶子。洗一洗可以盛酒、盛油、盛牛奶。要不,放牧牛犊时我们每人带上一瓶水,再也不会挨渴了。”
“你不是打碎一个了吗?”我问。
“我细看过了,那一个特别脏,没法用。”他回答。
我哑口无言。但心里不服气,觉得他是个没见过好东西的小气鬼。“好吧。那你打最后那个小瓶子。”我只好让着他,“那小瓶子是敌人的小崽子。打!”
他不知是早已看上了那个小绿瓶子,还是这会儿才突然喜欢了,非但不打,反而跑过去拾起来左右端详一下,满意地揣入怀里。
他的举动大伤了我这个鼻涕大王的自尊心。娃娃军里还没有人违抗过我的命令呢。我一气之下上去抢他装入怀里的小酒瓶。他的领口让我扯破了。争了半天,我到底比他大,把瓶子抢过来了。
“好,你不打,我打。”我夺他手里的投石器。
他没说话,气呼呼地一使劲,弄坏了投石器,扔了。
这一下,我可受不了啦,用脚丫狠狠踢他几下,然后把手里的瓶子——他特别喜欢的那个小绿瓶子摔了个粉碎。我觉得还不够解恨,便拿话激他:
“唐古特人重五钱,拄的拐棍重三钱,拾里拾外才八钱……”
这是当地人对唐古特人侮辱性的顺口溜。
我这一起头,娃娃军也扯着嗓门齐声喊。
伊席次仁的脸色非常难看,不知如何还口,只是来回重复着:“灰蒙古,傻蒙古……”
从此,我俩甭说再睡一个被窝,连见面都很少了。大概过了十来天,放牧牛犊时遇见了南浩特的双鼻子。他鼻翼有点宽,加上不论冬夏总穿一双双鼻子黑布鞋,所以给他起了绰号叫“双鼻子”。
他见了我打老远就扬手:“牛犊好放吗?鼻涕大王!”
“还好。可我们的大黄狗两天没回家了。”
“是呵,你的大黄狗八成是回不来了。”
“怎么啦?”
“它让人脱了衣服,在野外睡着呢。”
“哪会呢?是真的?”
“是真是假,你自个儿去看吧。我的鼻涕大王。”
“你看清是我家的大黄狗吗?”
“路过的行人还没把狗皮扒走前我看了,就是你家的大黄狗。”
“谁打死的?”
“那我倒没看见。不过,看出来是拿石头打的。脑门上嵌进一颗鹅卵石呢。”
“在哪儿呢?”
“在大路南边。”
大黄狗跟我形影不离,两天没回来我已经够着急了,没想到竟出了这种事。我不顾一切地朝双鼻子指的方向跑去。果然不假,一条被扒了皮的狗赤条条地躺着。虽然已经认不清了,但我断定是我家的大黄狗。在它脑门上真有一颗深深嵌入的鹅卵石。
是谁打死的呢?……小绿瓶子,投石器,鹅卵石,脑袋稀巴烂的豆鼠……我心中的疑团集中到伊席次仁身上,愈聚愈浓,很快变成一团可怕的云,骤然间电闪雷劈……哼!原来,唐古特人真狠毒!
娃娃军也都相信是伊席次仁用投石器打死的。很明显,用手能把鹅卵石嵌入脑门吗?而在我们当中用投石器能打得着自己脑袋的不少,能打得着狗头的却只有伊席次仁。不是他,能有谁呢!别忙,我让你厉害,让你报复!
第二天,我带着娃娃军找到了在野外放牧牛犊的伊席次仁。
“你为什么打死我的大黄狗?”
“我没打死你的狗。”
“给你脸,你倒把屁股亮出来了,嗯?”
“你才是亮屁股。”
“好一个小唐古特。明白点,我扒你的皮,就像扒这条狗的皮。”
“你来试一试,脏鼻涕王!”
看来,光动嘴不行,得来硬的。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这时,娃娃军一哄而上,把他摔倒了。
“你说,赖唐古特!你为什么打死我的狗?”
“不是我。你放开我,傻蒙古……”
“嗯!你不说?”
“傻蒙古,快放开我。”
“哼!还嘴硬。把他拉到石桌那儿去!”
我们揪着他的鼻子往耳子崖走去。
“他鼻子上没鼻环,不好牵。”双鼻子说。他可是个机灵鬼,点子多着哪,“他耳朵上不是有个现成的窟窿眼儿吗,穿上绳子牵着走,不挺省事?”他说着拔了根青芨芨草给我。
真是个好办法。我立即用这根芨芨草穿了他的左耳,在前面牵着走。伊席次仁哭哭啼啼不想走,动不动还踢我一下。
这时,一窝蜂似的跟在我们后边的娃娃军叽叽喳喳吵开了。
“没有犄角,没有鼻环,可还是有牵的办法。”
“那耳朵上的眼儿,就是为了让人牵才钻的呢。”
“这个眼是怎么钻出来的呀?”
“把铁丝烧红了钻的?”
“用大钉子钻的?”
“是狗咬的?”
一直沉默不语的伊席次仁一听这话突然大声说:“对!就是狗咬的。”他说完就地坐下,再也不动了。
我揪他,他唾我。我拉他,他骂我。突然,因为用力过猛,芨芨草把他耳朵豁开了。立时,鲜红的血流过了耳垂,流过了他的左腮……
这一下我们害怕了,一哄而散,四处跑开。说也巧,正在这时,我被牧马归来的阿兀(父亲)撞见了。他见我干了这种事,用套马杆狠抽我一顿。然后把伊席次仁放到马背上,他要把伊席次仁带回家治好伤,然后送到贡钦姨夫家,并声称要惩罚我。
谁知当天晚上,伊席次仁逃走了。第二天,大家骑马四处寻找,找了一天,才从五十里外的沙漠中找到了因饥渴而昏倒的伊席次仁。要知道,那时他才只有九岁。找回来后,他不吃一口饭,就要回老家,一有机会就往外跑。贡钦姨夫见这个情景,禁不住落泪,把他送回家去了。可是,贡钦姨夫从此再也没回到草原上。留在家里的姨姨也抱怨我,一见我就责怪:“你骂我呀!骂我找了个唐古特姨夫,嗯!”
唉!……这我可怎么办哪!
事情总是出人意料。伊席次仁走后的第三天晚上,那条我以为被他打死的大黄狗突然摇着尾巴汪汪叫着回来了。
唉!……这我可怎么办哪?
后来听说,伊席次仁回老家不久得了个什么病,死了。听了噩耗,甭提我有多伤心、多难过了。世上能有像我这样的大傻瓜吗?是我害死了他。要不是我欺侮他,伤了他的心,他能回去吗?要是还在这儿,怎么会死了呢?哦,我的伊席次仁!如今你在哪儿?我常常看到你那双清澈见底的黑溜溜眼睛在朝我眯笑着,我常常看到你朝我跑来,我常常看到你蓬松如云的卷发,可怎么也到不了跟前……呵,你让我太想念了。你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亲戚,你喜欢亲近我又格外相信我,可我……我怎么这样傻呀,真傻!
一眨眼工夫,二十二年过去了。
许多人都喜欢从那渐渐淡忘的孩提时期的记忆中找寻熠熠闪烁的珍宝。然而,我的脑海里盘旋的却是悲怆和悔恨……
译 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