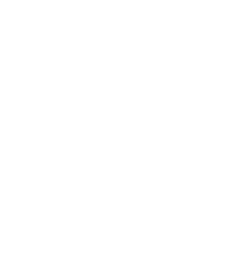1976年暑假,我回生产队参加劳动。队长看我干不了农活,派我到公社水利建设工地——前营河湾打大井。
前营村坐落在马头山东麓,村前是一条由西向东流淌的小河。大井就在村东面二里多的北河槽上。指挥部设在大井北边的土台上,椽檀搭架,绿色帆布盖顶。上面插满红旗,台口上方两角安装着高音喇叭,整日不停地播报着打井工程的进展情况。台口顶端红布插檐上写着11个金黄色大字——“后营公社水利建设指挥部”。台上一字排开摆着三张办公桌,麦克风放在中间。平时,里面坐着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她那甜嫩的声音不时从喇叭里传出,响彻整个工地。指挥部下方是井址,长100米,宽10米,两边每隔10米远,开出一条通道,供运料人车上下。
这次队里派我等五人去,是参加打大井决战的。开春时公社召开了三级干部(生产队、大队、公社)农业学大寨会议,根据上级精神,规划了全公社农田基本建设蓝图。拟用二到三年时间,在前营村东打一眼十亩大井,同时把欢子旺村台梁以北一带,后滩、后营、双山、芦草沟村中间宽阔滩地建成稳产高产田,打造塞外小平原。并且林带、水渠、公路配套。经县水利局技术员勘测,大井打到预定深度,截断地下潜流。井里水蓄到设定高度,可自流到滩里,浇灌万亩良田。当时,后营公社党委书记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张培合,他三十五六岁,敢做敢当,很有魄力。他认定这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工程,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干部、征得县委同意和支持,拍板定案。投入全公社人力物力,展开这一宏大工程。全公社42个生产队派出精兵强将,在前营、欢子旺村安营扎寨,早出晚归奋战在打大井的工地上。
我们后续人员到达后,立即召开了战前动愿大会。指挥部前42个小队一字排开,队前红旗迎风招展,旗上大字“青年突击队”“硬骨头小分队”“掘进尖刀队”……闪闪发光。主席台桌子后面坐了五位公社党委成员。张培合站起来,向全场人行了一个标准军礼后,拿起麦克风做动员讲话:“同志们,十亩大井建设到了关键时刻,据技术员测量,再挖一米深就达到设计标准。可现在井坑里出水多,4台抽水机昼夜吼叫也抽不净。希望大家拿出大寨人大战狼窝掌的干劲,发扬铁人王进喜的精神,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打成大井,造福子孙后代!后营公社八万人民看着我们呢!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授旗!”大队干部们精神饱满,健步上台接旗,敬礼,高举拳头表决心。台下台上喊声震天:“奋战一个月,打成十亩井!”
我们大队主任闫白子接过一面写着“铁人战斗队”的大旗,带领全大队打井队员走到工作面,把大旗插到井边,大声吼道:“小伙子们,我在台上说的话都记着吧?跟我上!”一个大队四个小队二百多人从行道奔到井底,挥镐动锹大干起来。我和李景瑞抬筐运土,一根柳木棍抬起二百多斤重的土筐,从十多米深的坑里沿着开挖的行道往上抬。前几次还行,越抬越觉得土筐重,压得几乎站不稳身。那时,李景瑞四十五六岁,是二连浩特市的干部,因犯了错误,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来村里已七八年。他看我抬筐吃力,就把筐子向他那边拉去,我顿感肩上的负重轻了许多。我心生感激之情,打起精神咬牙坚持。
整个大井里人头攒动,人们干得热火朝天。大队与大队之间展开劳动竞赛,比干劲、赛进度。指挥部专门设了流动红、黑旗,进度快的队插上红旗,进度差的插上黑旗。劳动的人们谁也不喜欢黑旗,使出浑身力量在井底拼命。同时相邻的三个大队相互拉歌,口号震天,歌声不绝。高音喇叭播报完工地消息后,又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我被这声势激励着,一股力量从脚跟腾腾升起,浑身来劲,和李景瑞抬着土筐穿梭于上上下下的运土队伍中。中午时分,食堂送来饭。每人一个六两重的玉米面窝头外加一碗小米稀粥。大家三下五除二吃了饭,爱热的躺在沙地,喜凉的睡到树荫下沟湾里午休。我和李景瑞在一处沙地坐下,他掏出大烟斗抽了几口,说:“抬筐可是一项重体力活,一定要当心,千万别闪了腰。”他还说小时候在煤矿干活,到潮湿阴冷的井下铲煤,生了痔疮,到现在一疼起来难以忍受。他侃侃而谈,和我说生活,谈古今。短短的午休结束后,我们又下到井里。两个人边抬土边聊,越说越投机,不觉太阳落山。肩膀上压起血包也不知觉,是李景瑞看到我上衣肩头处渗出血渍大声呼叫时,我才隐隐觉得有些疼痛。
晚上回到住地欢子旺村,在伙房吃罢晚饭,随李景瑞来到住宿的地方。一间平房,地上铺了厚厚的莜麦秸,墙边放着二十多个行李卷。李景瑞挨墙角打铺,他移开褥子,露出一处空隙,把我的行李铺开。然后点起煤油灯,从褥子下面掏出两本书,递与我一本,说:“读点做学问的书吧!以后会有用处的。”我接过来,是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打开书,竖行繁体字,我连这一“拦路虎”都对付不了,更别说弄清书中的内容了。李景瑞口含大烟斗,就着小油灯,专心读着一本厚厚的页面发黄的旧书。我问他读什么书,他说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时,其他人也陆续回来,有三四个围在一起打扑克的,两人顶头下象棋的,大多数人躺下拉闲话唱小曲。喧哗一时后,鼾声四起,一个个进入梦乡。李景瑞抬手拨拨灯花,看我捧着书犯傻,忙问:“怎么不读?”我一时无语,其实心里正翻江倒海:自己虽然高中毕业,可上学那几年不是批林批孔,就是下生产队学农,上课也学不到真正的知识。语文学的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语文老师想教点鲁迅作品,可没有教材,在黑板上整整抄了半个学期《狂人日记》。数学课学的是丈量土地、计算土石方、珠算等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内容。腹中空空,怎能读懂那么深奥的理论书籍。李景瑞见我面有难色,笑了,然后给我从头讲起,每晚讲一个知识点。从那时起,我懂得了认识的三个飞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内因外因、剩余价值、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知识。每天,我们俩一同劳动,一同吃住,在一盏煤油灯下读书。满屋脚汗味鼾声也不在乎,稳坐昏暗的小油灯下,游历于知识的海洋。我们俩相处融洽,成了忘年交。
一个假期过去,大井四壁的石头已砌出水面。大会战达到预期目的,我也该回学校教书了。李景瑞把我送到欢子旺村外,我们俩登上台梁,他向西望望前营方向,又转过身朝北指指一望无际的万亩滩,充满希望地对我说:“前营十亩大井打成了,水量充足。井水顺着大渠流入万亩滩,那平展展的一片将是米粮川。到时候林路渠配套、车马路上行、林带隔风沙、清水渠中流、田里五谷香、跨坡地桃红柳绿。那咱们这里就是蒙古高原上的小江南,咱们公社的老百姓可有好日子过了。”他的话深深打动了我:一个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人竟然有如此胸怀,他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远大政治抱负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志士仁人吧!我紧紧握住他那满是老茧的手,泪水夺眶而出。
时至今日,打大井那些日子经历的事情历历在目。李景瑞在人生的低谷不气馁,积极投身于火热的劳动中、用心学习政治理论,关心青年人成长,心中装着百姓,让我心生敬意。他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
文/宋福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