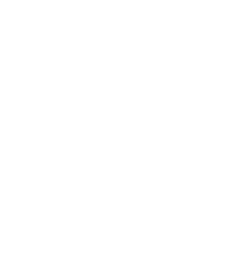最近,我参与了《库伦历史文化丛书》中的《库伦名人集成》的编译工作。当翻阅到第三部“名作家、编辑、翻译”初稿时,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打开文章一看,果然是她——我的师姐苏布道。
说起与师姐苏布道的相见相识,还有一段故事。那是1965年8月,我从家乡库伦旗的乡镇中学——额勒顺中学毕业,考入了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今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同时考上的还有我的同班同学白雪峰。当时,我们俩都从未离开家乡,更没有出过远门。虽然说考上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但一想到要去呼和浩特,还是觉得太遥远了。
那时候,我还不大懂汉语,更不会说,路上没有伴儿咋去呢?正在犯愁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布和朝鲁说:“你们不用担心。我妹妹苏布道是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的学生,她放暑假回来了。过几天她要来额勒顺看我们。到时候你们见面认识一下,约好时间跟她一起去呼和浩特。”
这下我们就放心了。过了些日子,布和朝鲁老师叫我们去他家,和他妹妹见面。苏布道那时候还不到20岁,身材修长,穿戴得体,梳着当时流行的齐耳短发,一双大眼睛,面容姣好,是个很漂亮的姑娘。我们后来才发现,她不但是班花,更是属于校花一级的美人儿,这是后话。
8月末,我和白雪峰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旗所在地库伦镇,见到了师姐苏布道。第二天大早,我们乘坐敞篷汽车抵达甘旗卡,又从那里坐火车,在大虎山倒车,后半夜在天津倒车,第二天上午到北京站,我们俩头一次出远门,头一次坐火车,典型的“乡下愣小子”,什么也不懂。一路上,从买车票、托运行李,到吃饭、喝水,苏布道师姐一路照顾我们,告诉我们注意事项。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笑话:到某一站,师姐下车买东西,回来一看我们俩不在,车都开了人却不见了,她以为我们下错车了,吓了一跳。仔细一看,才发现我们俩在车座底下铺了两张报纸,钻进去睡觉呢。她开玩笑说:“嚯!你们俩倒挺会享受,坐上了‘免费卧铺’了。”到了天津站倒车,正是后半夜,我们睡眼惺忪地被叫醒下车后,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怕走失,就紧紧跟随着苏布道师姐,就差扯着她的后衣襟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北京南站下车,乘20路公交车去永定门车站,途经天安门广场时看到了天安门城楼,我们激动异常。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北京就是天安门,天安门就是北京,真是恨不得跳下车把天安门看个够。师姐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说:“到永定门车站后咱们看改签车次情况,如果时间来得及,我领你们过来看看天安门。”但是事与愿违,当天下午由永定门开往呼和浩特的只有一趟车,不坐这一趟又得等第二天了。师姐安慰我们说:“既然到呼和浩特念书了,每年有寒暑假两个假期,回家路过北京,看天安门的机会有的是!”这话说的也是。
来到呼和浩特,来到学校,很快就开始按部就班地上课。师姐是翻译专业37班,我是翻译专业38班,两个班级的教室紧挨着,经常能见到。见了面,她就问问学习情况,家里来信了没有,并鼓励我好好学习等等。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直到1968年秋天,翻译专业37班毕业时,我有一次见到师姐,她告诉我说她被分配到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了。第二年,我也毕业了,被分配到昭乌达盟,两地相隔很远,联系也中断了。但是,我也从其他同学那里打听到她的情况。她在四子王旗当过警察,1974年,她丈夫部队转业回老家哲里木盟,她也随之调到哲里木盟广播电台工作,做过文艺部编辑、文艺部主任。这期间,虽然我们没见过面,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经常在报刊杂志上看到她的文学作品。她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很快成为内蒙古文坛上小有名气的女作家。
1984~1986年,师姐在内蒙古大学文研班学习期间,到赤峰体验生活,我们分别18年后才得以重逢。1985年,苏布道被选为哲里木盟文联副主席,她的小说散文集《云外有天》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秋叶》1988年获得自治区第三届文学创作奖“索龙嘎”奖。1999年,通辽市文联还主持召开了“苏布道文学创作作品研讨会”。
2001年夏,我去通辽出差,有一天早晨在哲里木宾馆大厅与师姐苏布道不期而遇,只寒暄几句,苏布道俨然以师姐的口吻批评我说:“之前好几次听说你来过通辽,为什么不去找我?”我支支吾吾,无言答对。师姐说:“好了,今天中午我做东请你吃饭,叫几个同学来作陪!”其实那天中午有人已经约过我,怎么办?为难之际,师姐快人快语:“不行!这次一定要答应我,给师姐一个面子!”她掷来绵里藏针的话,看样子没有商量的余地,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应允。席间,师姐讲了1965年跟她坐火车的路上发生的几件有趣的故事,包括白雪峰我们俩钻入车座底下睡觉,坐“免费卧铺”的事儿。还有一件事是,在天津站下车,刚出出站口,我大惊失色地喊了一声:“姐,我拿错别人的提包了!”师姐听后赶紧拉开提包的拉锁一看,里边装的是我的东西。没拿错呀!原来,我的天蓝色塑料提包经车站大楼霓虹灯一照,看上去是墨绿色的,害得我以为是拿错了别人的提包,真是虚惊一场。同学们听了,一阵哄堂大笑。真还有这么回事,都过了30多年,她还记得,记性真好。
2003年春抗击非典的时候,已经是通辽电台副台长、分管蒙编的师姐来电话说,她在《内蒙古日报》蒙文版副刊上读到我写的一篇题为《生活植根于爱的沃土》的散文,准备在他们制作的抗非典专题节目中请他们最好的播音员朗读这篇散文。后来,师姐把朗读的散文制成光盘寄给了我。师姐的关爱又一次温暖了我的心房。
2007年,传来师姐因病英年早逝的噩耗,我十分难过。我失去了一位十分可亲的姐姐和新闻同行,蒙古文文学创作队伍失去了一位很有潜力的女作家!
文/岱 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