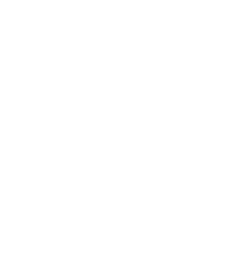画/杨 靖
前不久,几位文友同游大桦背,返回时在一位文友农村的父亲家借宿。晚饭时,一张方桌放在土炕中间,大家围坐在土炕上,边吃边聊。几杯酒下肚,兴致顿生。晚上,睡在炕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对土炕的记忆历历在目。
一
上世纪70年代,人们生活贫困,住房简陋,一盘大土炕便成为一家人晚上休息的地方。土炕上铺一张席子,一家人就睡在席子上。被子不够,兄弟两个盖一床被子是常有的事。夏天天热,睡起一觉来,被子早不知被谁蹬掉了,兄弟俩光着身子睡在炕上。冬天到了,家里冷得厉害,父亲提一箩头麦汁子,蹲在灶前熏炕。这时被子早已铺在炕上,吸收着土炕传导上来的些许温暖。
睡土炕,睡的地方很关键。夏天里,谁都想睡在靠近窗子的地方,因为窗扇支起来,外面丝丝缕缕的凉风钻进家里,靠窗子的人首先会享受到这一缕清凉。而离窗子远的人就只能忍受闷热了。到了冬天,又想睡在离窗子远一点的地方,因为,从窗子钻进的冷风首先“照顾”的是靠近窗子的人。于是,兄弟俩总是为睡的位置争执不休。最后争执的结果是母亲来调停,谁小由谁挑地方,所以,夏天靠近窗子的地方总是弟弟首选,而冬天,靠近窗子的地方总是父亲睡的地方。父亲不但撑起这个家,晚上还要为我们遮风挡寒。
土炕既是睡觉的地方,也兼具餐厅的功能。一张不大的炕桌,白天总放在炕中央。晚饭时,一家人围坐在炕桌前,边叨唠边吃饭。虽然饭菜简单,但是,那浓浓的亲情氛围却很热烈。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母亲纳鞋底,父亲捻毛线,我们在一边捣着乱。炕桌上的煤油灯闪烁着如豆的灯光,朦朦胧胧能看清每个人的脸庞。就是在这盘土炕上,母亲为我们姊妹7人辛勤劳作。夏天一茬布鞋,冬天一茬棉鞋,这是每年的必修课。被煤油灯熏久了,母亲鼻子发炎,留下了鼻炎的毛病,而且常常咳嗽不止。
二
我家窗子是三十六眼的小窗子,上面贴麻纸,下面有3块玻璃。春节到了,母亲撕掉窗子上的旧麻纸,再用糨糊贴上新麻纸。用剪刀剪几个窗花贴上去,东墙上也换上了两幅新的年画。屋里顿时熠熠生辉。几年过去了,生活好些的人家,沿土炕边画起了“腰墙子”。我们便磨着父亲母亲,也要画“腰墙子”。这天,画匠终于到了我家,我们兴奋异常。兄弟俩一个倒水,一个端颜料,几天后,我家的“腰墙子”画好了。“腰墙子”上画的什么都有,火车、花朵、鱼、人物、风景,让人欣喜不已。
“腰墙子”在我家的诞生,给土炕上、准确地说是给家里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趴在炕沿上,仔细端详着“腰墙子”,画匠真是神奇,一支画笔竟然画出了世间的万事万物。我们佩服了画匠好长时间。
三
就是在这盘土炕上,我们一个个长大。兄长都是弟弟妹妹的保姆,父亲母亲下地劳动了,一根橛子钉在土炕的边上,上面拴一根绳子,把弟弟妹妹拴在绳子上。母亲每天安顿兄长要看护好弟弟妹妹,往往是父亲母亲走后,兄长便偷着出去玩了,中午,父亲母亲回家后,土炕上拴着的弟弟妹妹早哭成了泪人,有时候屙下的屎和人搅和在一起。母亲只能在骂声中把他们洗干净。可是,过不了两天,这一幕又会重演。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的孩子都不少。晚上睡觉时,父母还要挨个数,看差了哪一个。一天,一户人家忘了数孩子,睡到半夜发现差了一个孩子,于是,便到处找,最后在场面的麦柴堆边找到了已经睡着的孩子。母亲拍掉孩子头上的麦柴,急急忙忙抱着孩子回家睡觉去。
土房子一年年陈旧,能挡住风,但有时候却挡不住雨,如果遇上连阴雨,一下两三天,房顶上便滴开了雨水,大人在炕上放个脸盆接雨,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
那时的生活条件虽然很差,但人的精神面貌却是现在的人无法比拟的。下午收工后,村里的篮球场上总有一群人在打篮球,晚上,红小兵都排成队在唱红歌。
时间过得真快啊,祖国的发展更快,现在农村人的居住条件和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了,这些飞速的变化是我这个已进入中年的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早晨,离开文友的父亲家,出门时,我不由又回头凝视那盘土炕,仿佛这盘土炕就是我家那盘土炕,一股暖流又一次涌上我的心间。文/李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