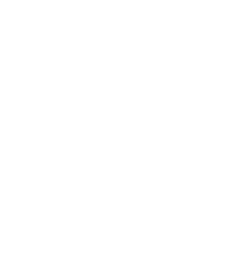中国有七个鲁迅:迷惘的青年,激愤的斗士,孤傲的文人,冷酷的批评家,幽默的旁观者,改造汉语的翻译匠,自我流放的精神导师。

中国有七个鲁迅:迷惘的青年,激愤的斗士,孤傲的文人,冷酷的批评家,幽默的旁观者,改造汉语的翻译匠,自我流放的精神导师。鲁迅的人格之丰富,对文学及历史影响之深厚,所处时代之起伏跌宕,使得后世每每谈起他,都难以全面。鲁迅在人们的理解和记忆中不断被解构、重塑,甚至扭曲、窄化,从课本里被大书特书到日渐淡化乃至剔除。这一系列的变迁,都让我们不禁反思: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鲁迅?
他的好斗,是为弱势者而斗

●林贤治(诗人、学者,代表作《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
新京报:你曾在文中写过:“鲁迅的灵魂,永远骚动着、挣扎着、叫啸着;这是一具自由的灵魂,大灵魂。”怎样走近鲁迅的“灵魂”?这样的“灵魂”在当下的社会,对于个体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
林贤治:灵魂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总和,或者说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它是一面镜子,有反映、借鉴的功能。面对鲁迅的灵魂,既可以观赏,也可以从中发现我们自己与鲁迅之间在人格、思想、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和距离。我说“鲁迅死于二十世纪而活在二十一世纪”,是说:第一,鲁迅当年所面对的,有许多我们今天仍然要面对;第二,鲁迅作为一个启蒙者、战斗者的存在,对于我们仍然具有“范式”的意义。
新京报:后人对于鲁迅的研究和叙述不断重塑着对“鲁迅”的理解,其中有标签化、片面化、崇高化、窄化鲁迅等诸多倾向。这是否能够解释,为什么一提到鲁迅,当下很多年轻人甚至产生了反感?
林贤治:我不知道当下青年人对鲁迅反感者占多大比例。我想若有反感,大抵因为他们心目中的鲁迅,并非从研读《鲁迅全集》(不读《全集》很难全面理解)而来,而是来自传闻的影响。最常见到的结论是把鲁迅装扮成一个偏激的好斗分子、睚眦必报的小人。我想,不必讳言鲁迅的好斗。问题是他跟谁斗?他的“好斗”始终是站在弱势者立场上对强权、强势的一种反抗。在一个专制的、腐败的、普遍顺从的奴隶(鲁迅常常自称“奴隶”)国度里,唯有不屈的反抗精神,才构成解放的要素。
新京报:《鲁迅的最后十年》以“鲁迅的存在,其价值仅仅在于反抗本身吗?”一句话结尾。鲁迅的存在,其价值何在?弊端何在?(鲁迅自己说过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
林贤治:我从来怀疑鲁迅对后世的影响力,所以总是强调其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往往并不取决于自身的价值。鲁迅的写作,本意在改造这世界。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这就意味着作品本身其实已经参与了世界的变动,起到其固有的作用。相反,假如世界依然存留了当年他所面对的大量的黑暗事物,还能说他的作品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吗?
“一个强烈的生活者”

●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新京报:竹内好曾评价鲁迅说:“他先是把自己从那个时代以及中国的历史和传统里面拉出来,跟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国的社会进行对决,然后又把自己拉进去,跟自己对决,否定之否定。”这种反叛对于当下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否还有价值?
王人博:鲁迅对待自己和身处的历史与现实的认知与反思的方法可以用“抽离”和“重入”界定。他首先身在历史文化与现实之中,随身携带其生存环境给予他的一切特征。然后从此在中抽离出来与之形成对峙、对决。“对决”是以“对峙”为前提,所以鲁迅的方法永远是战斗式的。鲁迅与其他知识分子最大不同的是他的“重入”,就像好不容易从敌人的营垒中逃离,为了完成一个重要的使命重新返回的气概。鲁迅的重入是为了与自己对决。他这个带着一切旧痕的人最终成了两个自我之间的战斗。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鲁迅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大。他只能被学习,不可能被模仿。那些自称是鲁迅学生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鲁迅的山寨版。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忙得没办法把眼珠子转向自己。
新京报:鲁迅对于你个人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你说的“鲁迅既是药,又是毒”?
王人博:在这个现代性的世界里,我们也已习惯了热闹的孤寂。我们通常不愿意与人说心里话,总想用现代性的技术把自己的心包裹起来。经验交流能力的丧失,人会变得孤独。对我而言,越是孤独,就越会想起鲁迅。特别是在深夜,想点上一根烟,与他对坐把盏,看一看他看过的风景。
新京报:鲁迅的研究者竹内好说他是个“强烈的生活者”,如何理解“生活者”?
王人博: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有两次谈到他的一种矛盾心境:“一是要给社会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如此灰色。折中起来,是为社会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但我自己就不能实行,这四五年来,毁损身心不少。”他一生都在“为别人”还是“自己玩玩”中苦苦挣扎,被这两个扰人的东西撕扯着。他在日本仙台学医的时候,经常外出一个人偷偷地去看电影。他学医却写小说和杂文,也喜欢版画。有时候,他啥也不做、不写,只希望用无聊“从速地消磨”自己。这是一种最真切的生活。竹内好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的意思大致在此。
一场“爱与自由的悖论”

●李静(文学评论家,剧作家,代表作《大先生》)
新京报:你曾借《大先生》来展现鲁迅一生的精神逻辑是“爱与自由的悖论”,如何理解?
李静:这里的爱,是一种牺牲、舍己的对众生的爱,一种感激式的爱。感激,是鲁迅的一种沉重的情感。甚至在他对众生、对受苦人的爱里,也包含了这种人格化的感激式的爱,因此没有居高临下的成分,而近乎一种形而上的“还债”。这种道义感驱使下的爱,是一种自我克制与献出,自会与他雄猛精进的自由意志发生悖论的关系。
新京报:你曾写:“这个孤独伟大的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性永远属于现在进行时,其烈度不因时代变迁而稍减。望着他寂寥的背影,我感到如果再不走近他,就永远走不近他了。”走近鲁迅,为什么必须趁现在?
李静:现在是一个薄情的时代。任何一个深情的人,都会在这个时代里感到自己的多余、迂阔和挫败。意志稍有不坚,就要改掉自己的“毛病”,去拥抱时代。我要趁着自己跟这个疯子投契的时刻,赶紧抓住他——谁知道我会不会在下一刻变聪明,忘掉他,背叛他呢?
新京报:有人说:“鲁迅是一个不断和时代进行交流的人,他一直在碰触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如何理解鲁迅与时代的关系?
李静:鲁迅对中国传统精神暗面的揭示和建设性的整理,对西方文明开放刚健的“拿来主义”做法,以及他与时代之间既紧密又疏离、富有活力和营养的对话方式,生命力永存。今日许多中国学者对传统/西方二元对立的框架,要么一味膜拜,要么一味否定的思维模式,都不及他境界的万一。鲁迅对国人奴性入木三分的追剿,对言论自由、生存权利和民主政治毫不妥协的伸张,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格魅力和道德美感,仍是我们不竭的精神源泉。
以他之身,窥己生死爱欲

●羽戈(青年学者)
新京报:你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鲁迅的悲剧恰恰在于:在‘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民族魂’等种种政治加持与神化之下,他不再被视作一个常人。”你如何理解这种“政治加持”和“神化”的?
羽戈:试举一例。如《孔乙己》一文,民国年间,王伯祥编《开明国文读本教学参考书》云:“这样一个平常的堕落的酒徒,给作者这么一描写,遂使人深深觉得我国社会的冷酷和长衫帮的日即没落。”今天的教学大纲则指出:“讲授这一课,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封建文化毒害知识分子的罪恶,加深学生对封建制度的憎恨。”这一对比,可知问题出在哪里。
新京报:从前鲁迅被写进教材大书特书,如今又从教材中被删掉、淡化。你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羽戈:第一,哪怕鲁迅的身影渐次从教材淡出,但论文章数量,他在教科书中依然位居前列;第二,抛开文字,要说锻造人的思维,尤其是逻辑思维,鲁迅的文章绝非一流,其杂文从不以逻辑见长;他惯所用的批判手段,如影射、诛心、扣帽子等,都违逆了说理的法则,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之流,确乎该早早逐出教材。
新京报:鲁迅的当代价值或未来价值如何界定?
羽戈: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与破坏力,终将成为自由主义所不能承受之重。一言以蔽之,用自由主义与鲁迅联姻,乃是一场一厢情愿的误会。鲁迅之为鲁迅,即在于不能用任何一种政治观来定位、约束,他是一个人的反对党,永远的不合作者。在他身上,窥见了光明之下的黑暗、热烈之下的无聊,同时窥见了自己的生死爱欲。(文/ 张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