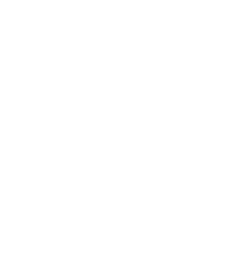沈继光,1945年生于北京羊房胡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美术系,于1987年举办个人画展。曾参加日本举办的"中国现代画家油画展"。1992年应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之邀,举办"胡同之没"黑白摄影展。1997年举办"家园·沈继光、邢国珍油画展"。2009-2012年在三味书屋先后举办个人艺术展"走不上的地平线--我与油画"回顾展、"心在天壤间"摄影作品展、"借草--逃往诗意的栖居地"设计作品展。
沈继光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用相机记录北京古城残片到行走于中国大江南北,为失落的乡野老屋留下影像,而今已是年逾七旬,他的新书《心在天壤间:光影三十年寻踪》可谓其艺术人生的总结之作。照片中的诸多物象看上去已然颓败,内里却流淌着永恒的古色,此间的事态之变和人情之美被默默记录。书页间悄然浮现的是布衣老者的中国情愫和当下日渐消逝的田园记忆,黑白的影像不失情味的色彩,淡淡的文字难掩内心的澎湃,是为一部兼具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的佳作。
光影三十年寻踪:归宿之诠
✪ 沈继光著/摄

▲墓地(1987年/新疆帕米尔高原)
在世界屋脊的荒原大漠上,独行,没有了方向和距离,只有恐惧包围着我。我,似乎知道我要寻找的东西,渴求的眼神搜索着,不放过难能一见的隆起的小丘或躺倒的半块枯骨……
无意中走进了一块起起伏伏的古老墓地。这片墓地宛如戏剧舞台的层层平台和台阶,不过,它是由白沙泥和红沙泥堆砌而成的,上面还雕着一种造型独特的泥塑,我全然辨别不出这泥塑到底是什么、像什么、寓意是什么。为什么非要辨别得出?也许,正因为无法辨别,它才更能昭示墓下所埋亡者的灵魂,那深得不可穷尽的灵魂。不是吗?
停留了两小时,用完了两卷胶卷。那是生与死的命题,那是灰、白、土红和黑的组合,庄重、肃穆至极。从晨曦到黄昏,这一天感受的力度和密度几乎让我不能承载。但,我还是在我能承载的那部分中付出了勇气而承载了。

▲毡房(1987年/新疆帕米尔高原)
不进毡房,已经窥出毡房主人的心境。毡的那纯质,那厚实,那针脚,那图案……它们都默默地说着话,闪露着神情。

▲等长途车的老人(1987年/新疆帕米尔高原)

▲废墟大石(1987年/北京)
您一定听说过圆明园。它有多大?四下望去,苍苍茫茫,不见边际。它囊括了不易数清的殿阁楼台、亭榭馆轩、廊桥摆渡、沼野旷坡、稻禾远村……是为当时罕见的园林建筑的集大成者,被誉为"万园之园"。
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园中珍宝后,纵火焚毁了圆明园,这座园林自此成为废墟。伟大的园林,躺倒了,也该是伟大的园林废墟吧!可后来,经由我们的手,又毁掉了这废墟,毁掉的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个情结、一派气象,不可复制。六七十年代,许多画画的人(我自在其中)常来这一带写生。这里没有门,不用花钱买票,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荒野大木和残柱断石"入画",按艺术家的眼光,这里是有品位的画境。近些年,经人工肆意修葺装点,那大气象渐渐一块一块地悄然流失了。

▲古墓(1987年/新疆帕米尔高原)
墓,在干燥少雨的荒漠中历经岁月,苍老消损,我看到了。但,我不满足于看到,我更愿意将它看成一幢朴拙的民居,宽敞通达,出入余裕;或看成一个城堡,拥有圆浑的穹顶、拱门和逶迤的墙垣;抑或看成一处遗迹,细读那残存的砖石和穴中的古代文字,以放大历史的斑痕;甚至将它看作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戏剧的巨大舞台设计,准备上演那摇魂荡魄的人生戏剧……
当眼前之物不再是单一的"用"和"意"时,我们兴许会获得类似解放般丰满、惊喜、辽阔的感觉。试一试,怎么样?

▲依然恢宏(1987年/新疆某故城遗址)
有着近千年历史又废弃了近千年的城池遗存,依然巨大,依然恢宏。面对它,我和我手中的相机感到无能为力,我无从把握,无从下手;我呆呆地站立,呆呆地走动,不知所措。或许,这正是一切深具伟大品性之伟大者给予人们的一种威严、震撼、挑战与考验?抑或是一种启蒙与拯救?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从一开始的"把握"与"下手"的自傲又无措的状态,渐渐地、静静地转入了虔敬、倾听、细读、渴望并吮吸那伟大气息的状态。
后来,竟也鼓起勇气举起相机,试着寻找一些角度、一些对比、一些有意味的形式……尽力拍下了我所能感受和理解的那一部分的"伟大"。二十年后,我再次凝视这个画面,觉得应该把那次拍摄时心理状态的转变写下来,以为自省。因为只有自己甘于低下头来,良久后,才能真正认识大地上的伟大。

▲一抔黄土(1987年/新疆喀什)
"古人祭在庙,不在墓。死者之魂,亦与生者之心相通,乃得显其存在。逮及三世五世,死者之魂与生者之心已渐疏远隔绝,则宗庙中的神位亦移去。年代既久,斯神魂亦失其存在。故中国人所重在生,不在死。""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此为中国人对死生问题千古永传之名言。""就个人之小生命而言,则皮肤骨肉之身生命必有死,而心情德性之心生命,则可永传无死。"(钱穆《晚学盲言》)
读着好书,凝视着画面,起草着图注,浑成一体,感觉自己又走了一步。

▲泰然(1987年/新疆帕米尔高原)

▲墓门(1987年/新疆帕米尔高原)
"当我们存在时,死亡不存在;死亡存在时,我们已不存在了。"这话似乎非常对。但我又想,话里所说的"我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我们的躯体还是我们的灵魂?是指我们存在时曾经以不同形式的语言表达的思想与情感,还是我们留给世上一些人的影响与记忆?……追究细问,上面那话就值得推敲了。
雨果写道:"如果死亡对人来说是一切的终结,那么,人在世时的所作所为就是无关紧要的了。""我,是个灵魂。我清楚地感觉到,我交到坟墓中的东西,不是我。那个我将要他往。大地,你不是我的深渊!""他往"--雨果的灵魂深嵌在他不朽的小说、戏剧、诗歌的字里行间,尽管他在1885年去世,但他一直结结实实地存在着,依然活得那么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