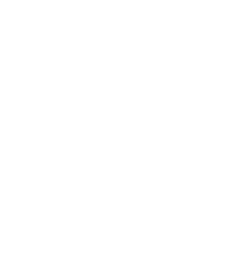汽车停在村口,我们想问路,左顾右盼,不见一人。时候已接近中午,村子好像仍熟睡未醒。
过去的村子可不是这样。每天天刚蒙蒙亮,空气和鸟儿醒了,负责打鸣的鸡醒了,树和草醒了,院子里的猪啊羊啊牛啊马啊都醒了。女人们让炊烟缭绕在村子上空,男人们边洗脸边琢磨这一天地里要做的营生。简单吃过早饭,上学的背起书包,下地的扛起铁锹或锄头,也有赶牛牵马套车的,村道上瞬间就热闹起来。然后就有年轻妈妈抱着吃奶的孩子,坐在院门口的石头上晒太阳。老爷爷老奶奶也出来了,闲不住的下地劳动,也有三五个聚在一起,家长里短聊着。也说些七荤八素,但没有贬低谁嘲笑谁的意思,就图个穷开心。后来,为了生活更美好,有人外出打工赚钱去了。当打工赚钱成为潮流,村里的青壮年越来越少,走着走着,就只剩老人和小孩儿了。随着乡村小学的整合,很多村子没有了学校,孩子无法就近上学,父母只能连孩子一块儿带到城里。很多村子再不见留守儿童,闲时聚在村头的,基本是老人,他们调侃说,六十岁左右,就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在村里,种地的人大都上了年岁,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似乎永远不到退休年龄。有些老人也可以不种地,有社保,有医保,在外打工的子女隔段时间会回来探望,并带回足够的吃喝与零用,但他们觉得,如果不种地,就对不住自己农民的身份,更对不住土地。在赛罕区,一位82岁的老农仍顶着秋天的太阳,和从城里歇工回来秋收的儿子一家在玉米地里一个一个往下掰玉米棒子,我说为什么不雇收割机,老人说一是得花钱,再者地不多,自己也想活动活动筋骨,要不闲着难受。大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宿命。
一次,在摩天岭上看农民碾扬收获的豆子,场面上也是没有一个年轻人。我们看着传统的劳动场面稀罕,他们看着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稀罕;彼此没有隔膜,畅快地谈论着村庄的过去和现在。老人们也担心将来,担心他们老了,更老了,不能下地劳动了,死去了,这些土地由谁来种?头罩红头巾的大娘跪在地上,仔细翻捡混杂在碎豆荚皮和沙土里的那些新鲜绯红的莲豆,真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几年,虽然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农业政策也越来越好,为鼓励农民种地,各种补贴也是层出不穷,但仍吸引不住年轻人,他们不愿和土地做朋友,依然选择在城里打工,吃着城里花钱买的馒头,想念自家地里出产的小米、莜面、土豆。
五月初下乡去清水河县。所到之处,很多院落大门紧闭,一把锈迹斑斑的锁头,紧锁着满院的寂寞和荒芜,了无生气。有些院子虽然看起来也是无人居住,但打扫得很干净,向阳处还种着绿油油的韭菜或葱,说明院主人会常回来看看,这让人心里多少得到一点安慰。一个院子里正在装修旧窑洞。主人是一对儿淳朴又热情的老夫妻,他们带我看院墙外新种的海棠树,给我讲水库里的鱼有多好吃,还邀请我秋天来他家院子里品尝葡萄。
不远处的另一处院子里,一条狗,一畦菜,两个像做手工一样认真劈柴的老人,悠闲自在的乡村生活场景。老大爷已经七十九岁高龄,边劈柴边给我讲门前扬水站的故事。老人记忆力非常好,说这扬水站建于1969年到1972年的人民公社时期,建成后试用了一次,感觉投入太大,就再也没有用过。五十年后的今天,扬水站像一座天桥岿然不动,站成天地间一道风景,陪伴着这些曾经为它出过力、流过汗的老人们。
这次,见到一位特殊的农村老人,他叫刘三堂,人称“小香米之父”。他是农民的带头人,是土地的守护神,是农村和土地的希望。他把儿子刘峻承从繁华的大上海召唤回来,和他一起种地,一起把小香米做成大事业,彻底改变家乡面貌,让年轻人重新认识农村,认识农业,从而爱上农村和农业。在一块正在播种的谷地里,负责田间统筹的小王,大学毕业后同样选择在城里打工,可越打越没劲,成天就是想着多挣钱,根本没有什么人生和事业规划。经过一番思考,他选择了和他的父辈一样,与土地和粮食打交道。如今,很多和小王一样有创业精神的大学生,陆续被年届七十的刘三堂吸引到农村这片广阔天地,施展他们的才华,从而实现远大抱负。刘三堂也退而不休,总是骑着摩托车上山去巡视,以便把积攒了一辈子的劳作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大学生们。
村里也有不简单的老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颐养天年。